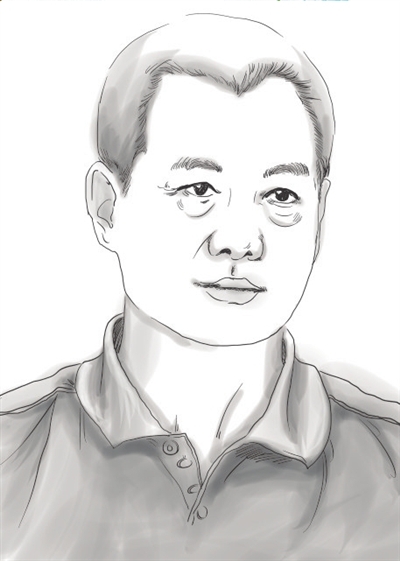赤子崔军
——记武警水电指挥部
 |
|
1991年5月25日,时任国务委员李铁映(中)参加羊湖电站开工典礼(左为方长铨、右为崔军)。 |
 |
|
1988年授予少将军衔时同贺毅(右)合影。 |
 |
|
崔军出生的窑洞。 |
 |
|
1948年10月14日,崔军和同学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合影(中排左一为李鹏、左二为崔军)。 |
 |
|
1977年12月3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右一)和时任水利部部长钱正英(左二)视察潘家口,崔军介绍工程情况。 |
 |
|
1999年10月3日,“4821”留苏同学合影(后排右三为崔军)。 |
 |
|
崔军和夫人黄小珊在家中。 |
原副主任兼参谋长崔军少将
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子,是1948年21名留苏学生之一。他说,我的出身,注定命运要与苦难同行。
他是武警水电指挥部少将,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为水电奔走请命。
他是在文革中饱受折磨的老人,内心并不怨恨,自认为“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
44年的水电生涯,他走遍了山川,先后参加狮子滩、下硐、紫坪铺、鱼嘴、青铜峡、石门、潘家口、引滦入唐、刘家峡、万安、峡口、天生桥一级二级、三峡、冯家山、宝鸡峡、大山口、羊卓雍湖等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参与白山、龙滩、二滩、葛洲坝、李家峡、水布垭、隔河岩、安康、鲁布革、漫湾、向家坝等工程的咨询工作。
1
印象
当记者在北京永定路的武警总医院南楼一科709室见到崔军时,他正步履蹒跚地挪出病房门口迎接。
“我的左眼看不见了。”他说。
记者看到,他的左眼眼睑完全耷拉下来,只剩一道细缝。现在,崔军的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0.2。此外,他还在经受着糖尿病的折磨。
上午9点15分,护士来给他测血糖。
“10.6,偏高了。”护士叫他首长。在记者看来,人们或许很难将眼前这个孱弱的耄耋老人同将军联系在一起。他是武警水电指挥部原副主任兼参谋长,1988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武警水电少将军衔;1999年,由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勋章后离休。
少将崔军在医院喝水的杯子,是一只老才臣豆腐乳玻璃瓶子。因为有些时日了,瓶子口上生了些许黑垢。他的夫人黄小珊说,他就爱这个,保温杯他也不用。
“要说干净,就这个干净。”他说。
文革期间,他被造反派折磨,前妻梁珍也受牵连,被称为“反革命臭婆娘”,夫妻感情也因此滑向不可挽救的深渊。1978年,梁珍带着小儿子与他离婚。
后来,经叶剑英之女叶楚梅介绍,同现在的妻子黄小珊结婚。
崔军在拍照的时候总是不笑,记者在翻看他的回忆录《田夫之子》扉页上的照片时,几乎都是这样的表情:眉心揪成一个“川”字,撇着嘴,心事重重的样子。但有两张照片例外,一张是1999年10月3日,“4821”留苏同学合影,他和罗西北、林汉雄站在一排,咧着嘴笑了;另一张是1997年10月18日,一家老小在家里照了个全家福,崔军面容和蔼宁静地笑了。
“最近有什么新闻?”吃饭的时候他问记者。
于是,记者和他聊起最近的工业明胶问题。他说,这些事都是共产党自己搞出来的,长期这样下去,老百姓怎么能再信任你?
他忧心忡忡,心里总装着事。眼睛看不见了,还在读书,写读后感。他给武警水电指挥部现任的领导同志写信谈部队的管理和体制问题;在走访和参观水利水电工程后给有关部门和领导写信提意见。他常忧心,如今的“做官”人,握着人民赋予的权力以权谋私,和老一辈革命家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
他从毛泽东时代走来,始终保持了一个老革命的风骨。即便他做到武警水电指挥部参谋长时,他的大儿子还在北京公主坟城乡贸易大厦当一名普通的工人。有一天他见到49岁的儿子,一问才知儿子已经退休了。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你儿子走个后门?他说,走后门就不是共产党员干的事!
2
生世
他是中共早期高级干部之子,父亲崔田夫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父亲原名崔文宪,1935年毛泽东接见崔文宪:
“你是个大字不识的田夫,为什么取个文绉绉的名字叫‘文宪‘呢?”
后来,崔文宪就变成了崔田夫。
1928年,崔军出生在陕西省绥德县崔家湾镇铁茄坪村一个没有门窗的窑洞里。这个村子近百户人家,全部姓崔,但姓崔的长工照样要给姓崔的财主干活,受他们剥削。
此时正值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高度警惕共产党人,实行白色恐怖。而就在崔军出生的半年前,父亲崔田夫,这个从未踏进过学堂大门的穷长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崔军说,我的出身,命运注定我要与苦难同行。
1934年,陕北游击战争形势紧张,6岁的崔军连同母亲赵应清和3岁的弟弟一起,被国民党抓进监狱,作为人质,来诱捕时为陕北特委书记的父亲崔田夫。
尽管遭受严刑拷打,赵应清始终不肯供出丈夫的下落。“我母亲头上、脸上、手上都是伤,晚上躺在谷草上,翻身都困难。”
国民党没有办法,在关押了他们母子3人一个月后,故意将他们放出,并派人跟踪监视,以便抓捕崔田夫。
为了不连累别人,这个农村小脚妇女带着崔军和弟弟沿路乞讨、流浪。此时的陕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人相食。当母子三人流浪到陕西绥德和清涧两县交界处时,同一直尾随的地下党员接上头,白天躲藏、夜里赶路,几经辗转才回到苏区。
从此,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土包子”吃上了“供给制”的饭,成了“公家人”,也因此在革命圣地延安接受革命教育的洗礼,树立了影响崔军一生的勤俭作风和奉献精神。
3
“4821”
1948年,崔军同李鹏、邹家华、罗西北等21人一同赴苏联留学,简称“4821”。同行的,还有叶挺、叶剑英、项英、刘伯坚、高岗、王稼祥等国家领导人的子女。
电影《红樱桃》里面那个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就是他们呆过的地方。他报考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和李鹏、贺毅、林汉雄、罗西北同一个系,四个人分别报了勘探、设计、施工、机电四个专业。他们憧憬着,等他们学成归国,定能把一个大水电站从勘探、设计、施工、安装、调试到发电全部包下来。
没想到,这次留苏的经历,文革中给他带来致命一击。他常忍着心绞痛、头晕去挨批斗、劳动改造,接受无产阶级的“再教育”。戴高帽、住牛棚、背语录、挂牌游街、挨打受骂、妻离子散,被折磨成了皮包骨。
文革时,他成为“4821”这个苏修“特务组织”21名成员中的一分子。
他身上挂着“杀人犯、苏修特务崔军”的铁牌子,戴上二尺多高的高帽,穿着纸糊的写着各种侮辱人格词语的衣服游街,接受人们向他吐口水、扔石子和砖头瓦片。陪斗时,他戴一顶用15圈钢筋做的高帽子,需要四个人托着才能前行。他被造反派强摁头,被人从背后一脚踢致腿弯,跪下。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造反派蜂拥闯入崔军的家,将他的技术资料连同从苏联带回来的书籍、毕业证书、生活照片和笔记撕碎、扔了一地。崔军在苏联和外国师生的合影,和他在黑海休假时和同学游泳晒太阳的照片,都成了他里通外国、生活腐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
一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在银川联合召开批斗自治区“走资派”大会,他被拉去陪斗。一颗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石子,击中他的左眼眼眶,眼睑立刻肿胀,内出血使眼圈乌黑睁不开,眼角裂开一条口子,鲜血糊住了眼睛。
在一个黑沉沉的夜里,他开始对这场大革命产生怀疑了:“我是红得发紫的人呐,怎么就变成了反革命、特务?我热爱群众啊,怎么就成了群众斗群众的幕后操纵者和野心家?”
他从苏联回来,满腔热血地准备报效祖国和人民,可祖国和人民回应他的是“苏修特务”。那种不被信任的极大冤枉,几乎让他痛不欲生。
“尤其是在灾难降临的时刻,往往死比生更容易,但是我必须活着,人一旦死去,就永远无法解释清楚应该澄清的事实。”
他选择活下来。
“你恨那些整你的人吗?”记者问。
“我不恨的,那不是他们的错。”
时过境迁,他和他20位一样被蒙在鼓里的同学后来才知道,“4821苏修特务案”是中央三办立案的大案子,由康生亲自主抓,逮捕崔军、罗西北的指令也是康生亲自下达。
1982年1月,中组部向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写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
2008年,“4821”60周年,崔军到满洲里市新国门参加落成剪彩,车到满洲里,60年前乘火车路过满洲里火车站及苏境边防的情景再一次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这是崔军一生中最最难忘的时刻。
4
水电生涯
他把44年的水电生涯,概括成做了两件事:“钻山沟”和“跑工地”。
1980年以前,他在各个工程点的山沟沟里转,大城市根本不去,有时候会到北京,开个会就走人。1980年以后,他脱离施工单位当了领导,说是住在北京,实际上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跑工地”。
1955年,崔军以优等成绩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系学成回国。他想着要到基层去,到生产一线去锻炼,向广大工农学习,于是立刻向组织写了书面报告,要求离开北京,到狮子滩的生产第一线。经水电总局局长李锐直接安排,1955年10月5日,他抵达重庆狮子滩水电站工地,担任厂房工区副主任兼主任工程师。那个年代的水电站施工,机械化程度低,靠的是人拉肩扛和满腔的革命热情。
1958年,狮子滩工程竣工,崔军又马不停蹄被调往下硐电站担任工区副主任兼设计和施工的总工程师。三年后,下硐电站发电,他又随同工区原班人马转往紫坪埔工地,出任施工总工程师,没想到却遭遇了他的第一个“滑铁卢”。时值“大跃进”,经过两年多奋战、用竹筋混凝土筑成的导流明渠被汹涌的岷江水冲得七零八落……
青铜峡水电站同样作为“大跃进”的产物,由于土法上马和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当时工程曾出现了不少质量问题和缺陷。由于工程需要,1963年水电总局将崔军从四川紫坪铺工程局总工程师任上调入青铜峡工程局任副总工程师。
文革住牛棚、戴高帽一晃就是三年过去了,随后工程局调往陕南石门水库,继续接受批判戴罪劳动又是五年。直到1974年的一天,时任陕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的李瑞山路过石门水库,听工友说起崔军来,李瑞山恍然大悟,这个饱受折磨的人原来是自己的老领导、陕北人民的老掌柜崔田夫的儿子,于是决定将他调离青铜峡工程局,到陕西省水电局。至此,崔军才得以从文革浩劫的梦魇中解脱,重新走上他梦萦魂牵的水电生涯。
1975年,崔军“二次把军参”,转入基建工程兵61支队,在潘家口一干就是四个年头,三班作业,大病一场。1978年50岁的崔军被诊断肺癌,后来肺癌排除了,在301医院割除了胆囊,后又带病工作。
1980年进了北京武警水电指挥部,从过去单纯的第一线施工到机关的管理领导工作,生活才开始走上正常化。
5
“婆婆嘴”
李锐在《田夫之子》的序言里,这样形容崔军:1992年以后,(他)被安排多坐机关,少下工地,他就‘常用婆婆嘴,处处管闲事’。原来电力部的一些老同志跟他开玩笑时也说:“你这个崔老总,坏就坏在嘴上了。你要是像那谁一样,把部长都当了。”
他一生中,仗义执言,从不怕得罪人。
记者问起,他眉毛一扬:“我又不想当官,我是搞技术的,所以得罪人我不怕的。现在成了老百姓,更加不会怕了。”
这个“婆婆嘴”还很“固执”。为出这本回忆录,因为书中涉及了从毛泽东到李鹏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的历史,电力出版社认为“政治敏感”。为此双方“磨牙”近三年,他坚持认为自己的回忆录尽管是一本“豆腐账”,但绝没有半句虚言。出版社社长拗不过他,说他“固执”。他说:“我就是固执,上至毛泽东下到李鹏,那时候,我见到过毛泽东呀,他给我题字,你把它弄掉,这一段我怎么写呀!当时李鹏和我是同学关系,这是历史呀!李鹏当了官以后我就再没写他。”
崔军的这张“婆婆嘴”,常常让人“讨厌”,有些地方又让人不得不服。这一点在天生桥梯级电站建设中他提出的“崔氏方案”上得到了印证。
天生桥梯级水电站,包括一级和二级,建在黔桂交界处的红水河上。原设计方案是,先利用红水河雷公滩落差来建天生桥二级低坝。1982年,崔军在现场考察了一个月之后,提出了与原方案相左的四条建议,即被61支队技术干部命名的“崔氏方案”:
一、无论是从能源利用还是从施工难易程度上考虑,都应先建一级电站,形成大水库,既能防洪又能提供二级电站的发电流量。
二、如果仍坚持先开发二级,就要下决心修改原设计方案。具体做法是:将低坝下移2公里,厂房上移2公里;将地面厂房改为地下厂房,设在2号支洞附近。
三、如果按照已批准的设计方案,总概算8.9亿到9亿难保,更谈不上实现“提前一年截流、提前一年发电、节约资金5000万元”的目标。
四、这样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必须采取高度机械化施工。
“崔氏方案”基本上推翻了原设计方案,因此时任武警水电指挥部主任的贺毅也没法拍板,随后方案汇报到了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鹏那里,但有关方面考虑到设计方案被推翻后不仅部队无法进驻、国家计委审批将更加困难等原因,最终除了第四条外,其余三条均未被采纳。
后来,天生桥在施工中遇到的问题都被他言中:厂房三次因地质滑坡移动,隧洞在开挖中遇到地下河、溶洞、暗河、断层,1985年12月24日发生的特大塌方事故更是酿成48人死亡的惨剧。
2000年下半年的一天,曾在天生桥发电后去现场考察的老同学罗西北给他打来一个电话,对他说:“当时你提的修改方案是对的。”
6
回归
离休后的崔军,终究还是闲不住,又不服老,所以只能继续干着在别人看来得不偿失的“傻事”。他奔走在水电建设一线,充当了水电部队的“广播员”、“通信员”、“情报员”,依然用他那张“婆婆嘴”,处处“管闲事”。从1989年底到1997年底的10年中,他给部长和中央领导同志送报告写信不下百封:五谈如何为水利水电队伍分忧解难、谏言二滩水电站及雅砻江梯级开发、反映三峡和小浪底工程建设问题。
他说坏事有时变成好事,他在文革中经历的所有苦难让他明白,意志上也得到锻炼,逐渐从盲目崇拜中解放,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并立志一生要为人民做点实在事。
崔军一生坎坷,苦辣酸甜尝遍,晚年时却能平静对待一切,不伤心、不生气、心情开朗、精神充实。
尽管疾病缠身,他还自嘲地打趣自己:“心坏、无胆、糖尿病,它(病痛)奈何我不得。”
晚年时,他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当别人都知道如何顺应大环境而明哲保身的时候,他却还在阐述、批评、伸张、争辩,生大可不必生的气、发大可不必发的火、失去大可不必失去的安宁、得罪大可不必得罪的人,真正是“不识相”得很。但他说,好在夫人黄小珊能懂他,她是一位好妻子也是一位好战友。
他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管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要从心灵深处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他始终以“长工的儿子”、“农民的后代”自诩,因此从武警水电指挥部副主任、参谋长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没有一点失落感,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貌,忘掉职务、放下架子,回到平民百姓之中。
送记者出门,他一边挪着小碎步,一边和记者打趣说:“现在我乐得一身清闲,什么也不管,就管我的202(202是他在位于北京六里桥的武警水电指挥部家属院的门牌号)”。说完,开怀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