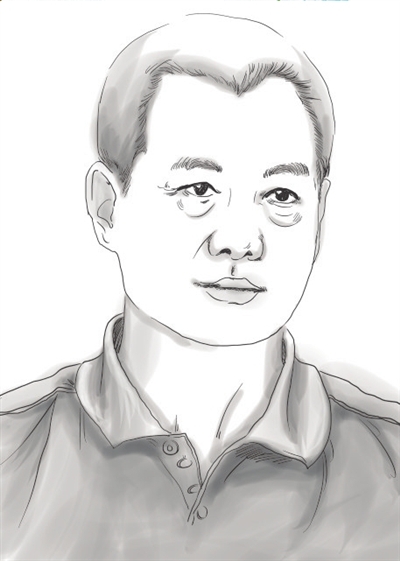原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魏廷铮:真正的三峡大考还未到来
2010/8/5 8:56:19 新闻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真正的三峡大考还未到来
—— 原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魏廷铮谈三峡“大考”
这次支流的灾害不少都是山洪。更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农村规划中,没有很好地把洪灾因素纳入考虑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特约撰稿白阳 | 北京报道
7月20日早晨八点,洪水以每秒7万立方米的流量,超越1998年洪水峰值,进入三峡水库。此时,年逾八旬的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原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平静地关注着这座2003年开始蓄水、通航发电的三峡水库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考”。
1949年7月,魏廷铮跟随有“治江泰斗”之称的林一山奔赴武汉治水。正赶上汛期,武汉被淹得一塌糊涂,乘坐的火车在水里面跑。从这一刻起,他就和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陪同毛泽东、邓小平几代领导人考察长江,提出了长江流域的完整治理开发规划。他还亲自主持设计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而三峡工程从规划到设计完成,则耗费他近40年心力。
如今,面对这次大考,这位在长江流域治水之路上走过大半个世纪的学者型官员,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三峡究竟为长江水患治理带来哪些效应?长江水患治理还面临哪些困局?近日,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魏廷铮。
这只算一次“小考”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三峡工程面对的这次“大考”?
魏廷铮:这只算一次“小考”,但产生的是“大考”的效应。从三峡大坝本身的安全性来讲,现在只是“小考”。现在上游来的洪水流量7万立方米/秒,这在宜昌也就是十多年一遇,而三峡大坝的防洪标准是百年一遇。真正的大考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洪水。百年一遇的流量就是83700立方米/秒,比今年的7万还要多13700,到那时水库的水位蓄到165.9米。
但对防洪能力而言,这是三峡的一次“大考”。1998年上游来了68000立方米/秒的流量,下面就淹得一塌糊涂。今年上游不仅来了7万立方米/秒的洪水,而且洞庭湖、鄱阳湖、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降水,都比1998年来得更集中。这一次跟1998年洪水规模差不多,上游的洪峰还稍大一点。
但是今年的长江堤防淹没区,基本安然无恙。1998年淹没区蓄的洪水大概是八九十亿立方米左右,蓄的水跟这次三峡水库差不多。可以说,1998年洪水是淹在农田里,现在是蓄在三峡水库里面,当时那么多水量要是蓄在三峡里,防洪也不会那么紧张。今年把1998年的问题解决了,不就是大考的效应么!
《望东方周刊》:刚提到“千年一遇、百年一遇”这些不同的标准,当初在设计三峡工程时,对它的防洪能力,设计的极限究竟是多少?
魏廷铮:三峡的防洪标准是按百年一遇设计的,当上游来的洪水达到83700立方米/秒,下泄的流量是56700立方米/秒,剩余蓄在水库;如果是千年一遇的洪水,上面来的流量是99000立方米/秒,下泄大概7万立方米/秒流量,下游防洪要受点影响,这是从大坝的工程安全标准考虑,保证大坝的水位不超过175米。实际上,大坝能挡万年一遇的洪水,就是105000立方米/秒。历史上万年一遇的洪水发生在1870年,洪水流量是110000立方米/秒,这是真正的大考,那时候的洪水如果现在来的话,三峡能把110000削弱到70000。这几个标准设计时就有,只是在不同条件下存在。
《望东方周刊》:三个标准具体来说对抗洪意味着什么?
魏廷铮:百年一遇的洪水,中下游防洪要保证安全,长江的干堤,主要的城市不能垮,这是要跟国家保证的。千年一遇的洪水,要配合应用中下游的分蓄洪区,主要城市不决口。万年一遇的洪水,下面要配合得多一些。总的一条就是,有了三峡工程以后,不能再发生毁灭性的洪水灾害,这是三峡工程建成后的目标。这也是三峡初步的功能,将来上游不是还有几十个水库么,要配合起来统一调度的话,中下游的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作用,紧张的抗洪抢险就不需要了。
泄洪背后的冲突
《望东方周刊》:有舆论质疑三峡工程的泄洪,是以下游为壑,增加了中下游的防洪压力,从规划设计目标考虑,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魏廷铮:现在水利部要求,三峡来水流量7万时,下泄4万流量,保证荆江大堤和沿江重要堤防的安全,保证洪水不上堤,不到警戒水位。最终是为了使三峡保留更多的库容,来更大的洪水,也能装下。现在221亿立方米的库容只蓄了70亿,这算是非常安全的防洪调度。
从三峡发电公司角度来说,可以蓄得更多一些,最好下泄流量在两万五,水库可以充分利用来发电。不过,防汛指挥部发调令给三峡公司决定是否开闸,对指挥部来说,库容越大越好。
《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三峡的防洪功能和发电功能之间怎么协调?
魏廷铮:这个应该由国家来协调,照顾各方面,求得最大的综合效益。中央1958年就有过一个针对长江流域规划的决定: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规划是统一的,全面发展,既要照顾防洪,也要照顾发电,也要照顾航运,几个方面的关系都要照顾到。
《望东方周刊》:现在是谁在协调?由长江委出面吗?
魏廷铮:长江委现在协调不了,应该由国家综合部门来协调。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是国务院的机构,以前主任是李鹏总理,后来是朱镕基总理,再后来是温家宝总理,现在变成常务副总理李克强。
《望东方周刊》:有媒体报道,2008年三峡集团公司曾为了发电,在汛期蓄水,一度没有执行长江委的调度令,今年在抗洪中表现却很积极,你怎么看?
魏廷铮:2008年这次蓄水还是适可的。145米的水位没有动,正好来了一场洪水,跟今年汛期一样。当时觉得不蓄,放下去就可惜了,三峡公司就蓄了一点。这实际也不是三峡公司自己要蓄的,是湖北、湖南两省提出来,你的水不能放下来,否则,我就要上堤防汛。湖北省首先提出,你要保证我的防汛安全,水库要蓄水。这样,三峡才蓄了大约几十亿立方米的水。
支流为何险情不断
《望东方周刊》:这次长江的干流,在三峡的调节下,相对安全。但支流似乎险情不断。有人认为是湖泊的消失所致,你认为原因在哪?
魏廷铮:湖泊对洪水有调蓄作用,但这个功能不大。下雨的时候湖水慢慢地涨,等到发洪水的时候已经涨满。这就要把湖泊围起来,让它干掉,洪水来的时候把水放进去。现在就是洞庭湖全干了,也就200亿立方米库容,况且不可能全干了。同时长江的泥沙在江里流速快,大都入海了,到湖里水面一放大,水流减缓,容易淤积。这次支流的灾害和湖泊的消失,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次支流的灾害不少都是山洪。更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农村规划中,没有很好地把洪灾因素纳入考虑。随着支流附近的人口增多,一些地区觉得,人多了没办法,于是在一些根本不能住人的区域,硬要把人安排进去。结果山洪一来,冲毁一大片,不少地方人口不能及时转移,应对的措施也不多。
支流广大地区一定要做好国土规划,山沟里面多种树,少住人或者不住人,容易产生滑坡泥石流的地方绝对不能住人。要知道,山洪往往来不及避让,一个暖湿气流遭遇较强冷空气时,集中下100或200毫米雨,这是山洪期间气象的特殊性,但一些地方主政者不了解。这是思路的一个转变,以前说控制这些灾害,现在要多想怎么去避免,减少损失。
《望东方周刊》:支流灾情不断,也有舆论认为是地方配套资金不够,比如江西省,就说没钱修堤防了。
魏廷铮:不光是这样,江西有几个水库,比方说这次出事的抚河,有个廖坊水库,修低了。修建时主要有个思想,反对修高坝大库,坝修高了要移民,当时的移民条件不够、安排不好,移民多了要到他这里闹事,所以水库大坝尽量压低,但是防洪功能不管。另外修水电的人有一个思想:下面不想修,指望上面修一个龙头水库,上面蓄水,下面的不考虑。我们做流域规划的时候,都希望他修高一点。但最后地方自己设计的时候改低了。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改低?
魏廷铮:他不考虑综合利用,只考虑部门利益。坝修低了,工程就小了,花钱就少了,电量损失不多。从发电的角度讲,修高一点低一点影响不大,他要调节就修所谓的龙头水库。所以现在支流上普遍有这个问题,这些水库现在的库容防洪作用不大,只顾发电,太可惜了。
《望东方周刊》:历史遗留的防洪工程问题,需要解决的还有哪些?
魏廷铮:还有围堤,在湖区围的围堰,堤防标准很低,容易决口。最近九江说有险情,水利部解释说1998年九江决口的那个地方,今年没有决堤,是别的地方。其实九江那地方本来就没有江堤,原来是个湖区,后来围垦开辟了农场,好多中央机关的人下放到那里,把堤坝加固了一些,堤都是土堤。这次很多有水患的围堰,本身谈不上水利工程,都是自己围成垸子在里面种地,没有规划,也没有认真地按照安全标准做好。
毛病就犯在老是一刀切《望东方周刊》:这么些年来,你感觉我国整体上的治水思路,有什么变化?
魏廷铮:最早周总理提的防洪方针是,要“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尽量把水放下去,因为长江水量太大,像大禹治水那样,保证排水道、排洪道必须畅通。
《望东方周刊》:就是用大禹的那套方法?
魏廷铮:也不完全是。还要修三峡大坝,大坝是主体,负责蓄水。蓄和泄,两个都要搞。从形势来判断,泄水要放在前面,把水放到海里去,因为长江洪水都蓄起来不可能。
现在看来,蓄做得不够。现在全世界都在闹水荒。水资源能蓄要多蓄一点,能蓄的地方尽量蓄水。总之多蓄一点水有好处。
《望东方周刊》:蓄水程度为什么会不够?
魏廷铮:因为怕修高堤大坝。修了这些,会淹没一些地区,就要移民。当时怕修水库主要是怕移民,怕得要命。确实当时移民做得太差,对老人的安置,对民生的照顾,做得很不够。当时国家没钱,都要国家出钱,出不起。
《望东方周刊》:历史上一直有围湖开发的做法,1998年洪水过后,国务院提出过“退田还湖”的政策,这算是治水思路上的调整吗?怎么想起来推出这个政策?
魏廷铮:当时防汛的时候,说老实话,太急,哪些地方应该严防死守,哪些地方不应该严防死守,哪些地方应该分蓄洪,哪些地方应该确保,应该区别开。当时事情紧急,所以都要严防死守。回头再看有些地方不值得严防死守,应该让出来。我估计“退田还湖”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给洪水一个空间,人从河里、湖里把围垦的垸子退出来。
《望东方周刊》:有报告指出,当时“退田还湖”的政策推进速度特别快,有的是双退,人退,田也退。有的是单退,人退,田不退。最后似乎遇到了阻力。
魏廷铮:不合理的围垦要退掉是应该的,合理的当然退不了,一定要符合客观实际。任何事都得有规划,强扭的瓜不甜。最后双退的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单退,但是单退等于没有退,就是人换个新房子,在湖里照种不误,摩托车一骑,拖拉机一耕,种子一撒,庄稼成熟照收不误。
1998年以后,有好多时间都是依靠1998抗洪精神。但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现在中央要靠科学实践。任何事情主观意志是不行的。
《望东方周刊》:1998年抗洪后我们究竟吸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魏廷铮:1998年抗洪还是传统的方法,拼人力,洪水之后,中国科学家防灾减灾的研究成果,开始相应得到重视。但之后采取的措施含有多少科学技术的成分,很难说。
当时花了很多钱,在长江干支上搞“隐蔽工程”。就是哪个地方有漏水,有隐蔽的漏洞,就全面的打板桩,或者做防渗墙,不管好坏,一道修理,花了几百亿。
作用很有限。所谓隐蔽工程怎么找出来?隐蔽在哪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人早就总结了。堤防这个问题的影响因素很多,哪里有问题,哪里处理,需要加固的进行加固,不需要的再加固,没有意义。毛病就犯在老是一刀切,一个口号覆盖全面。
一大批科技力量没得到充分应用
《望东方周刊》:1998年的那些安全隐患现在都消除了吗?
魏廷铮:还没有大水来考验。今年水位比1998年要低三四米呢,武汉水位只是二十六七米。要到真正的保障水位,城陵矶是34.4米到35米,武汉29.73米,那时候才能检验出来。
《望东方周刊》:防洪体系需要科学性,实际上,从1998年开始,长江治水的理念,据说就已经由经验型向科技型转变,现在我们的防洪体系中,支撑防洪决策的技术条件如何?
魏廷铮:洪水的科学调度是有一套体系的,每一个洪水年份都不一样,但总能找到一些典型。现在软件这么发达,可以做大量的调度模型,最后由电脑来精确调度。一条河流像长江这样,至少有一百几十年的资料,准备十个、二十几个的调度模型,都可以编出来。但是,现在有很多资料,都没有很好地利用,没有编出像样的模型,这方面的科学技术开发很差劲。
《望东方周刊》:什么原因导致的?投入不够?
魏廷铮:说老实话,现在就是扯皮。各个部门,你考虑防洪,你考虑发电,你考虑航运,都是大部门,只照顾自己的利益,都想按各自的模型调度,最后出来的这个模型就行不通。
不是缺钱,这能花多少钱?主要是人的思想统一不起来。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一面。还是人的因素起作用,不要针锋相对,锱铢必较。应该是考虑它的综合效益,大家该让步的要让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部门利益。
《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其他难以协调的关系?
魏廷铮:涉及的部门跨了几个大部,地方又跨了几个省。而且越是小单位越要强调各自的利益。
比如湖南、湖北两岸的要求就不一样。长江的水位在关键的时候,要影响到洞庭湖和荆江的关系,原来两边争论的时候,长江的水位差一厘米,就要打架。湖南说我本土的水,也就是南水,我不怕,我怕北水,也就是来自长江的洪水,长江尽量少向洞庭湖进水。湖北就说你这个洞庭湖应该多分水,长江水位低一点,我好防洪。三峡大坝没起来之前,两家都维持现状不准动。三峡大坝起来以后,现在两家都在对三峡提要求,湖北要求汛期三峡泄流应该控制在十万立方米每秒以下,湖南说长江入洞庭湖的四个口,应该给控制起来。
连小地方像一个荆州和一个常德这两家的矛盾就不好办,原来常德说长江进水进多了,防汛受不了,要求控制。但是现在,它又缺水了,开始找三峡要求放水,三峡放水又只能进洞庭湖,到不了常德。这些矛盾有些是无知,有些是对科学的认识太缺乏了。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要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利害关系,进行科学调度。
《望东方周刊》:现在是否需要更高的层面来自上而下地引导技术开发?
魏廷铮:上面的人应该明白,不明白就容易瞎指挥。其实长江水利委员会有这么大一批技术力量,现在很可惜,没得到充分应用。此外,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弄钱,认真做技术开发的人少了,想方设法去弄钱的人多了,这就麻烦了。
—— 原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魏廷铮谈三峡“大考”
这次支流的灾害不少都是山洪。更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农村规划中,没有很好地把洪灾因素纳入考虑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特约撰稿白阳 | 北京报道
7月20日早晨八点,洪水以每秒7万立方米的流量,超越1998年洪水峰值,进入三峡水库。此时,年逾八旬的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原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平静地关注着这座2003年开始蓄水、通航发电的三峡水库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考”。
1949年7月,魏廷铮跟随有“治江泰斗”之称的林一山奔赴武汉治水。正赶上汛期,武汉被淹得一塌糊涂,乘坐的火车在水里面跑。从这一刻起,他就和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陪同毛泽东、邓小平几代领导人考察长江,提出了长江流域的完整治理开发规划。他还亲自主持设计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而三峡工程从规划到设计完成,则耗费他近40年心力。
如今,面对这次大考,这位在长江流域治水之路上走过大半个世纪的学者型官员,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三峡究竟为长江水患治理带来哪些效应?长江水患治理还面临哪些困局?近日,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魏廷铮。
这只算一次“小考”
《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三峡工程面对的这次“大考”?
魏廷铮:这只算一次“小考”,但产生的是“大考”的效应。从三峡大坝本身的安全性来讲,现在只是“小考”。现在上游来的洪水流量7万立方米/秒,这在宜昌也就是十多年一遇,而三峡大坝的防洪标准是百年一遇。真正的大考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洪水。百年一遇的流量就是83700立方米/秒,比今年的7万还要多13700,到那时水库的水位蓄到165.9米。
但对防洪能力而言,这是三峡的一次“大考”。1998年上游来了68000立方米/秒的流量,下面就淹得一塌糊涂。今年上游不仅来了7万立方米/秒的洪水,而且洞庭湖、鄱阳湖、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降水,都比1998年来得更集中。这一次跟1998年洪水规模差不多,上游的洪峰还稍大一点。
但是今年的长江堤防淹没区,基本安然无恙。1998年淹没区蓄的洪水大概是八九十亿立方米左右,蓄的水跟这次三峡水库差不多。可以说,1998年洪水是淹在农田里,现在是蓄在三峡水库里面,当时那么多水量要是蓄在三峡里,防洪也不会那么紧张。今年把1998年的问题解决了,不就是大考的效应么!
《望东方周刊》:刚提到“千年一遇、百年一遇”这些不同的标准,当初在设计三峡工程时,对它的防洪能力,设计的极限究竟是多少?
魏廷铮:三峡的防洪标准是按百年一遇设计的,当上游来的洪水达到83700立方米/秒,下泄的流量是56700立方米/秒,剩余蓄在水库;如果是千年一遇的洪水,上面来的流量是99000立方米/秒,下泄大概7万立方米/秒流量,下游防洪要受点影响,这是从大坝的工程安全标准考虑,保证大坝的水位不超过175米。实际上,大坝能挡万年一遇的洪水,就是105000立方米/秒。历史上万年一遇的洪水发生在1870年,洪水流量是110000立方米/秒,这是真正的大考,那时候的洪水如果现在来的话,三峡能把110000削弱到70000。这几个标准设计时就有,只是在不同条件下存在。
《望东方周刊》:三个标准具体来说对抗洪意味着什么?
魏廷铮:百年一遇的洪水,中下游防洪要保证安全,长江的干堤,主要的城市不能垮,这是要跟国家保证的。千年一遇的洪水,要配合应用中下游的分蓄洪区,主要城市不决口。万年一遇的洪水,下面要配合得多一些。总的一条就是,有了三峡工程以后,不能再发生毁灭性的洪水灾害,这是三峡工程建成后的目标。这也是三峡初步的功能,将来上游不是还有几十个水库么,要配合起来统一调度的话,中下游的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作用,紧张的抗洪抢险就不需要了。
泄洪背后的冲突
《望东方周刊》:有舆论质疑三峡工程的泄洪,是以下游为壑,增加了中下游的防洪压力,从规划设计目标考虑,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魏廷铮:现在水利部要求,三峡来水流量7万时,下泄4万流量,保证荆江大堤和沿江重要堤防的安全,保证洪水不上堤,不到警戒水位。最终是为了使三峡保留更多的库容,来更大的洪水,也能装下。现在221亿立方米的库容只蓄了70亿,这算是非常安全的防洪调度。
从三峡发电公司角度来说,可以蓄得更多一些,最好下泄流量在两万五,水库可以充分利用来发电。不过,防汛指挥部发调令给三峡公司决定是否开闸,对指挥部来说,库容越大越好。
《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三峡的防洪功能和发电功能之间怎么协调?
魏廷铮:这个应该由国家来协调,照顾各方面,求得最大的综合效益。中央1958年就有过一个针对长江流域规划的决定: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规划是统一的,全面发展,既要照顾防洪,也要照顾发电,也要照顾航运,几个方面的关系都要照顾到。
《望东方周刊》:现在是谁在协调?由长江委出面吗?
魏廷铮:长江委现在协调不了,应该由国家综合部门来协调。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是国务院的机构,以前主任是李鹏总理,后来是朱镕基总理,再后来是温家宝总理,现在变成常务副总理李克强。
《望东方周刊》:有媒体报道,2008年三峡集团公司曾为了发电,在汛期蓄水,一度没有执行长江委的调度令,今年在抗洪中表现却很积极,你怎么看?
魏廷铮:2008年这次蓄水还是适可的。145米的水位没有动,正好来了一场洪水,跟今年汛期一样。当时觉得不蓄,放下去就可惜了,三峡公司就蓄了一点。这实际也不是三峡公司自己要蓄的,是湖北、湖南两省提出来,你的水不能放下来,否则,我就要上堤防汛。湖北省首先提出,你要保证我的防汛安全,水库要蓄水。这样,三峡才蓄了大约几十亿立方米的水。
支流为何险情不断
《望东方周刊》:这次长江的干流,在三峡的调节下,相对安全。但支流似乎险情不断。有人认为是湖泊的消失所致,你认为原因在哪?
魏廷铮:湖泊对洪水有调蓄作用,但这个功能不大。下雨的时候湖水慢慢地涨,等到发洪水的时候已经涨满。这就要把湖泊围起来,让它干掉,洪水来的时候把水放进去。现在就是洞庭湖全干了,也就200亿立方米库容,况且不可能全干了。同时长江的泥沙在江里流速快,大都入海了,到湖里水面一放大,水流减缓,容易淤积。这次支流的灾害和湖泊的消失,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次支流的灾害不少都是山洪。更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农村规划中,没有很好地把洪灾因素纳入考虑。随着支流附近的人口增多,一些地区觉得,人多了没办法,于是在一些根本不能住人的区域,硬要把人安排进去。结果山洪一来,冲毁一大片,不少地方人口不能及时转移,应对的措施也不多。
支流广大地区一定要做好国土规划,山沟里面多种树,少住人或者不住人,容易产生滑坡泥石流的地方绝对不能住人。要知道,山洪往往来不及避让,一个暖湿气流遭遇较强冷空气时,集中下100或200毫米雨,这是山洪期间气象的特殊性,但一些地方主政者不了解。这是思路的一个转变,以前说控制这些灾害,现在要多想怎么去避免,减少损失。
《望东方周刊》:支流灾情不断,也有舆论认为是地方配套资金不够,比如江西省,就说没钱修堤防了。
魏廷铮:不光是这样,江西有几个水库,比方说这次出事的抚河,有个廖坊水库,修低了。修建时主要有个思想,反对修高坝大库,坝修高了要移民,当时的移民条件不够、安排不好,移民多了要到他这里闹事,所以水库大坝尽量压低,但是防洪功能不管。另外修水电的人有一个思想:下面不想修,指望上面修一个龙头水库,上面蓄水,下面的不考虑。我们做流域规划的时候,都希望他修高一点。但最后地方自己设计的时候改低了。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改低?
魏廷铮:他不考虑综合利用,只考虑部门利益。坝修低了,工程就小了,花钱就少了,电量损失不多。从发电的角度讲,修高一点低一点影响不大,他要调节就修所谓的龙头水库。所以现在支流上普遍有这个问题,这些水库现在的库容防洪作用不大,只顾发电,太可惜了。
《望东方周刊》:历史遗留的防洪工程问题,需要解决的还有哪些?
魏廷铮:还有围堤,在湖区围的围堰,堤防标准很低,容易决口。最近九江说有险情,水利部解释说1998年九江决口的那个地方,今年没有决堤,是别的地方。其实九江那地方本来就没有江堤,原来是个湖区,后来围垦开辟了农场,好多中央机关的人下放到那里,把堤坝加固了一些,堤都是土堤。这次很多有水患的围堰,本身谈不上水利工程,都是自己围成垸子在里面种地,没有规划,也没有认真地按照安全标准做好。
毛病就犯在老是一刀切《望东方周刊》:这么些年来,你感觉我国整体上的治水思路,有什么变化?
魏廷铮:最早周总理提的防洪方针是,要“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尽量把水放下去,因为长江水量太大,像大禹治水那样,保证排水道、排洪道必须畅通。
《望东方周刊》:就是用大禹的那套方法?
魏廷铮:也不完全是。还要修三峡大坝,大坝是主体,负责蓄水。蓄和泄,两个都要搞。从形势来判断,泄水要放在前面,把水放到海里去,因为长江洪水都蓄起来不可能。
现在看来,蓄做得不够。现在全世界都在闹水荒。水资源能蓄要多蓄一点,能蓄的地方尽量蓄水。总之多蓄一点水有好处。
《望东方周刊》:蓄水程度为什么会不够?
魏廷铮:因为怕修高堤大坝。修了这些,会淹没一些地区,就要移民。当时怕修水库主要是怕移民,怕得要命。确实当时移民做得太差,对老人的安置,对民生的照顾,做得很不够。当时国家没钱,都要国家出钱,出不起。
《望东方周刊》:历史上一直有围湖开发的做法,1998年洪水过后,国务院提出过“退田还湖”的政策,这算是治水思路上的调整吗?怎么想起来推出这个政策?
魏廷铮:当时防汛的时候,说老实话,太急,哪些地方应该严防死守,哪些地方不应该严防死守,哪些地方应该分蓄洪,哪些地方应该确保,应该区别开。当时事情紧急,所以都要严防死守。回头再看有些地方不值得严防死守,应该让出来。我估计“退田还湖”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给洪水一个空间,人从河里、湖里把围垦的垸子退出来。
《望东方周刊》:有报告指出,当时“退田还湖”的政策推进速度特别快,有的是双退,人退,田也退。有的是单退,人退,田不退。最后似乎遇到了阻力。
魏廷铮:不合理的围垦要退掉是应该的,合理的当然退不了,一定要符合客观实际。任何事都得有规划,强扭的瓜不甜。最后双退的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单退,但是单退等于没有退,就是人换个新房子,在湖里照种不误,摩托车一骑,拖拉机一耕,种子一撒,庄稼成熟照收不误。
1998年以后,有好多时间都是依靠1998抗洪精神。但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现在中央要靠科学实践。任何事情主观意志是不行的。
《望东方周刊》:1998年抗洪后我们究竟吸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魏廷铮:1998年抗洪还是传统的方法,拼人力,洪水之后,中国科学家防灾减灾的研究成果,开始相应得到重视。但之后采取的措施含有多少科学技术的成分,很难说。
当时花了很多钱,在长江干支上搞“隐蔽工程”。就是哪个地方有漏水,有隐蔽的漏洞,就全面的打板桩,或者做防渗墙,不管好坏,一道修理,花了几百亿。
作用很有限。所谓隐蔽工程怎么找出来?隐蔽在哪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人早就总结了。堤防这个问题的影响因素很多,哪里有问题,哪里处理,需要加固的进行加固,不需要的再加固,没有意义。毛病就犯在老是一刀切,一个口号覆盖全面。
一大批科技力量没得到充分应用
《望东方周刊》:1998年的那些安全隐患现在都消除了吗?
魏廷铮:还没有大水来考验。今年水位比1998年要低三四米呢,武汉水位只是二十六七米。要到真正的保障水位,城陵矶是34.4米到35米,武汉29.73米,那时候才能检验出来。
《望东方周刊》:防洪体系需要科学性,实际上,从1998年开始,长江治水的理念,据说就已经由经验型向科技型转变,现在我们的防洪体系中,支撑防洪决策的技术条件如何?
魏廷铮:洪水的科学调度是有一套体系的,每一个洪水年份都不一样,但总能找到一些典型。现在软件这么发达,可以做大量的调度模型,最后由电脑来精确调度。一条河流像长江这样,至少有一百几十年的资料,准备十个、二十几个的调度模型,都可以编出来。但是,现在有很多资料,都没有很好地利用,没有编出像样的模型,这方面的科学技术开发很差劲。
《望东方周刊》:什么原因导致的?投入不够?
魏廷铮:说老实话,现在就是扯皮。各个部门,你考虑防洪,你考虑发电,你考虑航运,都是大部门,只照顾自己的利益,都想按各自的模型调度,最后出来的这个模型就行不通。
不是缺钱,这能花多少钱?主要是人的思想统一不起来。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一面。还是人的因素起作用,不要针锋相对,锱铢必较。应该是考虑它的综合效益,大家该让步的要让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部门利益。
《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其他难以协调的关系?
魏廷铮:涉及的部门跨了几个大部,地方又跨了几个省。而且越是小单位越要强调各自的利益。
比如湖南、湖北两岸的要求就不一样。长江的水位在关键的时候,要影响到洞庭湖和荆江的关系,原来两边争论的时候,长江的水位差一厘米,就要打架。湖南说我本土的水,也就是南水,我不怕,我怕北水,也就是来自长江的洪水,长江尽量少向洞庭湖进水。湖北就说你这个洞庭湖应该多分水,长江水位低一点,我好防洪。三峡大坝没起来之前,两家都维持现状不准动。三峡大坝起来以后,现在两家都在对三峡提要求,湖北要求汛期三峡泄流应该控制在十万立方米每秒以下,湖南说长江入洞庭湖的四个口,应该给控制起来。
连小地方像一个荆州和一个常德这两家的矛盾就不好办,原来常德说长江进水进多了,防汛受不了,要求控制。但是现在,它又缺水了,开始找三峡要求放水,三峡放水又只能进洞庭湖,到不了常德。这些矛盾有些是无知,有些是对科学的认识太缺乏了。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要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利害关系,进行科学调度。
《望东方周刊》:现在是否需要更高的层面来自上而下地引导技术开发?
魏廷铮:上面的人应该明白,不明白就容易瞎指挥。其实长江水利委员会有这么大一批技术力量,现在很可惜,没得到充分应用。此外,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弄钱,认真做技术开发的人少了,想方设法去弄钱的人多了,这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