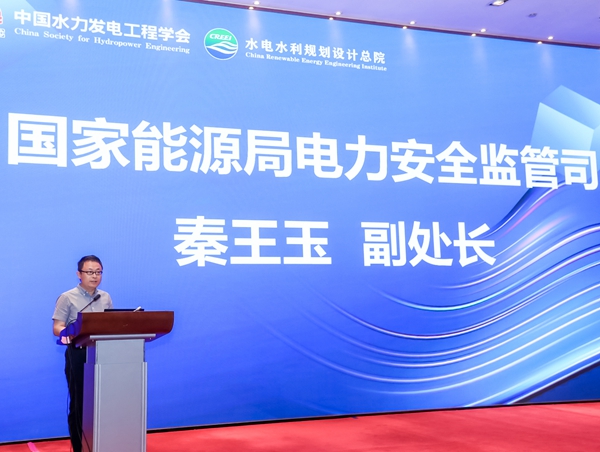如今的一个矛盾现象是:当科学正在飞速发展的时候,当地球正被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改造的时候,却出现一股强烈的反科学反正统 文化思潮。
这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存在的对科学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爱因斯坦大概是受公众尊崇的科学家的突出代表,这种尊崇 在当时是盛行的。德克赖夫(Paul De Kruif)于1926年在《微生物猎人》(The Microbe)—书中描述了激动人心的结果:科学家们现在可以缓解痛苦并增进人类健康。本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指出,人类由于把科学的思维方法应用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而得到了很大实惠。但是今天,这种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时代》周刊上有一篇文章以如下不 祥的口气开头:
“
科学家看来正在成为西方社会的反派角色。 我们在报纸上读到他们伪造和杜撰数据,我们看到他们在国会议员们面前为10亿 美元研究预算辩护。我们听到他们通过把大爆炸或某个亚原子粒子比作上帝,用充分的说服力践踏我们的情感。
”
美国《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社论提到《时 代》周刊的这篇文章时发表评论:
“
这是否反映了一种增长着的反科学态度?如果是,那么新上映的影片《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将没有什么助益。按照作者和导演的意图,这部形片包含强烈的反科学倾 向。有报道说,导演施皮尔伯格(S. Spielberg) 认为科学是“侵略性的”和“危险的”。
”
大放厥词的并不仅仅是局外人。众议院空间、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布朗(George Brown)在最近的讲话和文章里,看来已对科学的真正价值表示怀疑。据布朗观察,尽管我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领先,但我们依然存在许多社会弊病,如环境恶化和卫生保健难以承受。他说,科学“承诺的多于它能给与的”。戴森 (Freeman Dyson)似乎也有同感。
他在最近一 次普林斯顿讲演中提出,“未来若干年,如果对科学的攻击变得愈益强大和广泛,我不会感到吃惊,只要我们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性保持尖锐,只要科学继续普遍地沉溺于为富人建造玩具。”
尼科尔森(Richard S. Nicholson)在上述社论中发问,“这些仅仅是孤立的事件,还是一 种正在发展的潮流?”
科学丧失了显赫威信的进一步迹象是,美国国会最近对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的否决。虽然给出的主要理由是削减国家赤字的迫切性, 但人们不禁感到,这个决定表明公众对科学研究的信任水平正在下降。
正如斯诺(Lord C. P. Snow)于1959年指出的,一直共存着两种文化。在那些希望发展科学文化的人与那些声称存在“两种真理”的人之间,存在着长期的辩论。按照后者,伴随着认识过程的科学知识,存在着一种神秘的、精神的领域和(或)体验的审美及主观方面。这两种文化从未和平共处过。在最近数十年里,危及科学在社会中地位的公开抨击正愈演愈烈。
在哲学中,异议来自两个有影响的领域。第一,从库恩(Kuhn)到费耶阿本徳(Feyerab end)的许多科学哲学家提出,不存在什么像科学方法那样的事物,科学知识是相对于社会文化风俗的,范式转换由超越理性的原因造成,因此认为存在检验科学见解的客观方法这一早先信念是错误的。
这种批评显然言过其实。的确,科学相对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起作用,并且,在科学上我们不能作出绝对的陈述。但是,还存在检验见解的可靠标准和某些客观性判据, 这些都超出特定的社会文化框架。怎样解释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科学知识呢?科学中的特定见解不能说成是等同于诗歌隐喻或宗教信条,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它要接受实验结果的检验。
第二个抨击来自海德格尔(Heidegger)的追随者,特别是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如德里达(Derrida)、福柯(Foucault)、拉康(Lacan)和莱昂塔(Lyotard)等人。他们提出,科学只是许多系统中的一个虚构系统或叙事系统。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解构科学语言,我们发现不存在什么真实的客观标准。
海德格尔抱怨科学和技术正在使人非人化。福柯则指出,科学往往受权力机构、官僚和国家的支配,科学的政治和经济用途损害了科学保持中立的权利。这些批评有的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都夸大其辞。如果对客观性的选择是主观性的,如杲对真理不存在可作为依据的声言,那么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就不能说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肯定地坚持:力学原理是可靠的,火星是环绕太阳运转 的一颗行星,心血管疾病可以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采取预防措施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害。DNA结构并不是社会的制造物,胰岛素也不是文化的产物。
“现代性”的后现代批评家们反对16和17世纪产生的科学的唯理论者或唯基础论者阐释,或许确有道理。因为科学理论的不断成 长和修正表明,在科学内部“探求确定性”或 “终极的第一原理”是错误的。然而,他们走得太远了,抛弃了整个现代科学事业。认识自然和人类生活的科学方法,已经因为它的成功而被证明是正确的。我认为,它的前提更是正确 的。这种现代科学观发展到今天,它有些什么特征呢?
第一,科学预先假定存在客观方法,通过这些方法可以检验可靠的知识。第二,这意味着可以建立假说和理论,并通过有关的证据、合理一致的判据,及它们预言的实验结果,来确立这些假说和理论。第三,现代科学家发现, 数学定量化是建立理论的有力工具。第四,他们认为,在我们与可被发现的自然之相互作用中,存在着因果规律和因果关系。第五,虽然知识可能不是普遍的,但在知识超出纯主观的或文化的相对性并植根于探索者主观间和文化间的共同体的意义上,它是普遍的。第六,从科学的演进性和可否证性,可见其难以达到绝对或终极的陈述,科学是尝试性和可能性的,科学探索必须允许不同的解释争鸣。因而以前的理论可以受到挑战和修正。选择性的和建设性 的怀疑是科学观中的基本要索。第七在于认同这样的事实:科学研究发现的现象,其可能原因的知识可以被应用,强有力的技术发明可以被作出,这些都对人类大有益处。
然而,在拓展知识领域中起过巨大作用的科学方法,如今竟然受到猛烈冲击。特别是有关神秘学、超自然现象和伪科学的剧烈增长, 尤其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些领域提倡非理性和感觉论。据说,我们正生活在“新时代” 当中。与天文学并驾齐驱,存在着向占星术的回归;与心理学相伴随,存在着心灵研究和超 心理学的增长。超自然现象肆虐,科幻小说无边。这是太空旅行时代,它包括为外星人所劫持和来自其他星球的不明飞行物。超自然世界观的兴生,与科学世界观相对抗。伪科学提供的是在大众思维中与真科学相对抗的其他的解释,而不是经过检验的因果解释。超自然信仰的剧增,表明极度的反科学态度不是孤立出 现的,而是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态度和信仰1个组成部分。
《怀疑的调査者》(Skeptical Inquirer)杂志的读者,无疑都了解CSICOP(超自然见解科学调査委员会)在评估超自然见解和边缘科学(fringe sciences)见解中的突出作用。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对公众欣赏力给予科学调査、 批评思考和科学教育。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对反科学思潮的广泛增长给予同等关注。
最近数十年里,对科学最为尖锐的攻击,是怀疑科学对社会的利益。这些批评相当程度上基于伦理学原因,因为它们怀疑科学研究和科学观对人类的价值。以下列出10类此种异议。当然还有其他异议。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可能的核大屠杀而引起的巨大焦虑。这种恐惧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存在着来自核事故和大气核试验的放射性尘埃的某种危险,存在着政治或军亊首脑 (有意或无意)着手毁灭性核战争的威胁。幸运的是,眼下热核大屠杀的危险已经减少,尽管它肯定尚未消除。然而,此种批评造成了对科学研究的恐惧,甚至在有些地区,竟有人认为物理学家是恶魔,认为他们在笨拙地揭示自然奥秘过程中,企图毁灭这颗星球上一切生命形式。对核辐射的恐惧也波及核电站。切尔诺贝利事件加强了世界大部分人口的忧虑:核能是危险的,核电站应该关闭。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一座核电站正在建造,尽管法国和其他国家仍在继续建造核电站。于是,核时代已产生反核反应,过去科学家仁慈的象征爱因斯坦,某种程度上已被扭曲成一位嗜核战争者。虽然对核辐射的忧虑有的确实是正当的,但要想完全放弃核燃料(化石燃料的燃烧会污染大气),对满足世界能量需求,却未留有多少选择余地。这并不否认有必要寻找可再生的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但这些能源够用吗?

2.对科学的恐惧,还可在环境运动的某种过度行为中找到。尽管环境主义者强调生态保护是有根据的,但它往往导致惧怕人类技术不可修复地破坏臭氧层,惧怕温室效应将导致整个星球的没落。此种恐惧常常导致对一切技术的无理排斥。
3.在大部分人口中,存在着一种对任何种类化学添加剂的恐惧症。本世纪30?50年代,人们广泛认为“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可以通过化学来实现”,认为化学物质将增进人类健康。如今却相反,存在着广泛的毒性恐怖 ——害怕PCBs(多氯化联苯)和DDT(滴滴涕),害怕塑料和化肥,特别害怕各种添加剂,存在着世界范围的呼吁回归自然、回归天然食物和自然方法的运动。毋庸置疑,我们有必要当心未经检验的化学添加剂毒害生态系统,但我们不应忘记,化肥的有效使用导致绿色革命,导致食物产量剧增,从而减轻世界各地的饥荒和贫困。

4.对生物遗传工程的怀疑,是反科学增长的另一个方面,生物遗传研究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许多人担心,科学家会把新的有病毒的大肠杆菌菌链排入下水道,然后遍及生态系统,扼杀大量生命。里夫金(Jeremy Rifkin)及其他人因其“非人化”结果,已经提出禁止任何形式的生物遗传工程研究。施皮尔伯格导演的影片《侏罗纪公园》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生动例子。在这里,不仅人形怪物企图起死回生,而且人们都受到警告:正在无性繁殖恐龙的一位凶残的新科学家将释放毁灭这颗星球的不祥力量。尽管生物遗传工程可能确有某种危险,但它在治疗遗传病及创造新产品方面为人类提供巨大的潜在利益。合成胰岛素的产生即是证明。

5.反科学增长的另一个例子,是对正统医学的广泛抨击。这些批评有的在理。随着科学革命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能够延长人的寿命,但有许多人却违背其意愿活着,并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死亡权已作为一个基本伦理权益被提出来。医学伦理学家正确地指出,病人的权利往往为医疗界和法律界人士所忽视。在过去,医生被视为权威的象征,他们的智慧和技能是无可质疑的。但对如今的许多大事声张的批评家来说,与其说医生是救星,不如说是恶魔。对动物研究的广泛反感,表明了对科学的抨击。就算动物不应当受虐待或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但有些动物权倡议者竟主张禁止在动物身上做任何医学研究。

6.反科学的又一个例子,是对精神病学的愈益反对。萨斯(Thomas Szasz)在此无疑起了重要作用。由于他的著作,许多精神病人得以出院。克西(Ken Kesey)在1962年发表的《飞越疯人院》( One flew Over Cuckoo' s Nest)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往往正是精神病学家本人而不是病人有精神病。尽管似乎有确凿证据表明,有些病人确实患有行为障碍,表现出可以用抗精神失常药物加以缓解的症状,但如萨斯之类的许多人却否认存在精神疾患。

7.与抵毁公众对医学和精神病学实践信赖相伴随的,是“他择性健康疗法”现象的增长,从信仰疗法和基督教科学派到松弛反应、虹膜学、顺势疗法和药草医学。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医学科学在征服疾病、研制抗菌素和非常成功的外科手术等方面已取得了值得称颂的进展。这些都已成为人类健康的福祉。但现在医学科学自身的生存能力却受到了诘难。
8.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领域,是亚洲神秘主义的影响。特別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方神秘主义凭借瑜珈冥想、中国气功、古鲁斯以及唯灵论者闯入了西方世界,据说这些古老的智慧形式和疗法会以现代医学做不到的方式导致身心健康。不幸的是,这些所谓心灵疗法的可信的临床验证寥寥无几。我们所具有的,大多是奇闻轶事的描绘,但它们难以成为他择性疗法的客观检验。

9.另一种反科学形式是,甚至在髙等科学机构和教育机构中基要主义者信仰的再度流行。基要主义者怀疑科学文化的根基。在现代世界里,似乎正是宗教(而不是科学)以人类希望的面目出现。投入宗教的金钱比投入科学和教育的资金要多得多。特别有代表性的是,“科学创世论”和对中学里进化论教学的广泛政治抗议不断增长,尤其在美国。
10.反科学的最后一个领域是对科学教育的多种文化批评和男女平等主义者抨击的增长,在大学和学院中尤甚。多种文化论者认为,科学不是普适的或跨文化的,而是相对于它赖以产生的文化。据说,非西方的和原始的文化才如同西方世界的科学文化那样“真实” 和“有效”。这场运动主张科学知识的完全相对化。激进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对科学中“男性偏见”的指控认为,科学已成为“死去的盎格鲁- 撤克逊白种男人”的体现——从牛顿到法拉第,从拉普拉斯到海森伯。这些运动的过激论者提出,我们所必须做的,是把人性从知识的文化表达、种族歧视表达和性别歧视表达中解放出来,同样也从科学客观性中解放出来。当然,这些运动的正面贡献在于,它们企图使科学对更多的妇女和少数民族开放。其负面作用是,多种文化论者主张在教育中应弱化对严格智力标准的限制,而这种标准对有效的科学探索是至关重要的。显然我们必须认同历史过程中许多文化的科学贡献和妇女在科学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有些多种文化批评家却贬低客观科学的可能性。
我所列出的是万花简似的例证,它们显示了许多目前正在损害和威胁科学未来增长的倾向。它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为什么这会出现?那些相信科学方法和科学观价值的人该如何作答?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只能提出几种可能的解答。但除非科学共同体及与之有关的人愿意严肃地接受对科学的挑战,否则我担心反科学浪潮会继续上涨。在那些明显存在从科学研究中得到技术应用的地方,科学研究肯定不会被拒斥在外,至少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发现这些研究有用的范围内如此。但对科学方法和科学观评价的降低,对科学在文明世界中的长期作用只会有有害影响。
反科学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对公众进行科学本质教育的基本失败。在科学的目标中,对公众教育的必要性尤为重要。我们必须提高对科学探索一般方法的认识,提高它与怀疑论和批评思考的关系的认识,提高它对检验见解真实性的证据和理由的要求。我们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是提高这样的认识:科学方法不仅应用于专业化学科的狭隘领域,而且应尽可能推广到人类感兴趣的其他领域。

我们还必须提高对科学宇宙观的认识。运用科学研究技术,科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关于宇宙和人种的许多理论和一般表述。这些理论往往与大部分未受过挑战的神学观点相抵触。它们还往往与神秘的、浪漫的和审美的态度相悖。因此,对于多数科学家和科学解释家们来说,是到了解释科学告诉我们关于宇宙的知识是什么的时候了。例如,它们应当展示进化的证据,并指出创世论不能说明化石记录;应当展示思维的生物学基础的证据,而轮回转世说或不朽性根本不存在任何证据。除非科学共同体愿意公开解释和捍卫科学告诉我们关于生命和宇宙的知识,否则我担心它将继续受到大量无知的反对它的人的中伤。
在这个教育过程中,重要的是在学校和大众传播媒介中提高科学普及水平。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只占美国人口极少百分比的人通晓科学原理。英国、法国和徳国的情形类似,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完全不了解科学观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对公众开展教育,使他们懂得科学是如何发展的,以及科学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应当确信这一认识适用于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
专业化的增长已使得这一任务相当艰巨。专业化使人们集中精力于一个领域,使人们把他们的创造才能倾注于解决专门问题,要么是生物学中的问题,要么是物理学、数学或经济学中的问题。但我们必须同培养专家一样培养通才。大多数对科学的恐惧和反对是因为对科学探索的本质缺乏了解。这种了解应当包括重视我们知道的和我们尚不知道的东西。这意味着不仅重视我们现在拥有的全部可靠的 知识,而且重视怀疑的观点和态度。科学的解释者们必须从专业化中走出,走向对科学告诉我们关于宇宙和我们在宇宙中所处位置的知识的一般阐释。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在一定意义上,科学是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力量,因为科学家必须准备质疑一切,准备对任何声称要求证实或确认。
广大公众欢迎科学创新。每一个新发明或新产品,技术中的每一项新的应用(正面应用),都因为它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而受到重视。未受到重视的是科学探索的本质,和进一步发展科学批评方法,特别是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的必要性。除非科学界人士有足够勇气把科学方法和理性方法推广到他们力所能及的其他领域,否则我感到反科学思潮的增长仍将继续。

如今,这不仅是在实验室里工作、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的任务,它还是哲学家、新闻记者,以及在公司和政界关心科学对人类贡献的那些人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处在危急关头的正是现代思想本身。除非公司经理们和 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在过去 4个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并能继续在未来起作用,除非科学得到捍卫,否则我担心反科学的非理性增长会损害科学研究的生存能力,损害科学对未来的贡献。关键在于教育,不仅是学校中的教育,而且是传播媒介中的教育。我们必须提髙认识水平,不单对从小学到大学的学生,而且对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人。正是在大众传播媒介里,科学观往往被暴力、过分渲染的性、超自然现象和宗教偏见所掩盖。
现今世界是一个种种思想交锋的战场。在这个环境中,科学的信徒们必须有力地捍卫科学在人类文明中已经起过的和仍将继续起的可靠作用。反科学思潮的增长必须受到倡导科学优越性思潮增长的反击。科学家肯定不是不犯错误的,他们会犯错误。但科学不可估量的价值必须得到重申。我们必须以用科学观表达的理想来重新感召公众。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